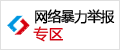从乡村到乡村
◇石华鹏
从乡村到乡村,我经历了城市这么一个驿站。
城市是一根扁担,一头挑着我出发的乡村,一头挑着我不断行走的乡村。它喂养了我二十多年,给予我生存的资本和生活的空间,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”,我有恙时它医治我的身躯,朋友来时它让我们的聚会变得时尚,它为我的孩子提供教育和交际的热闹……无论列举城市多少馈赠,于我而言,城市终究是物质的、现实的,我的灵魂我的精神时常从城市出逃,飘向遥远而永恒的乡村。
并不是我孤恩负德,并不是我对城市无情,而是乡村盛情于我,给予我生命,喂养我身体和灵魂的第一口奶。童年和少年,在乡村的风日里长养,触目为青山绿水,奔跑在大地田野,大自然是我的第一任老师,滋养我、教育我,一切自由自在。读到艾青先生深情的诗句:大堰河,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。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,抚摸我——我就想到我的乡村的雪和它宽大的手掌。艾青的大堰河是我们每个人的乡村。
从乡村出来,无论脚步走多远,精神再也难以离开乡村。这是为什么?我时常会想到这个问题,躺在城市的床上我会想,躺在乡村的床上我也会想。我知道,当我躺在城市的床上想这个问题时,我是想回到乡村去了;当我躺在乡村的床上想这个问题时,我是不舍我又要离开乡村了。
每次到乡村,首先复活记忆的是我的鼻子,农家饭菜的香、家禽牲畜的味以及大自然万物生长死亡的气息,与我儿时的气味重合起来。我以为乡村气息属于鼻子,而城市气息则属于耳朵——没完没了的轰鸣和喧嚣,各种现代的声响此起彼伏。
夏天,从热浪滚滚的福州到乡下采风,车停乡政府,下车一刻,熟悉亲切的乡村气息瞬间包围了我。凉风轻柔拂面,空气洁净,可以品出清甜、草木的味儿,似乎还夹杂傍晚炊烟的味道。车场边的林中不时有几声虫鸣和鸡鸣传来。远处,青山静然,天空阔远,夕阳的余晖染红了一片云朵。一切那么恬淡、自然。
我们住的民宿在离镇街不远的村里,由前村支书家的房子改造而成。房子建于20世纪90年代,三层,二十余米长,外露式长走廊,每层八九个并排小房间,如乡村中学的那种教学楼或乡镇政府的办公楼,最不像的是民居住宅。这一点让我好奇。
不过有一个好处,出房门,站在走廊上便可饱览田野景致:成片绿油的晚稻正在扬花灌浆,水塘的荷花开得洁白灿烂,溪水轻轻流淌,农人开着摩托车轰隆驶过屋前的省道,随后大地安静下来……
半夜,几只蚊子造访我,将我从睡梦中叫醒,再也睡不着,索性披衣出门,坐到廊上来。乡村的夜很静,虫鸟们都睡了,草木、稻禾、荷叶等的气息更浓。天上有半月,在薄云中穿行,月光如洗,离屋不远的205省道此刻变成了一条明晰的河。看着这条路河,我突然有些感触。这条宽阔平坦的路河,迎来送去,将一个宁静闭塞的乡村与城市连通了起来,但终究是送出去的多呢还是迎进来的多呢?
我出生的那个村子,直到前两年才有一条窄窄的水泥路修通,那条砂石路我走了好多年。乡村总会有路通往外面,我希望那条路慢一点,静一点,悠然一点。
很长一段时间以来,我们逃跑似的离开乡村到城市落脚后,一直做着两件事:一是将那个安静朴素、陈旧灰暗的乡村漠然地搁置在那里,不管不问,只自顾自地在城市里为前程和生活奔忙,以为自己属于城市了,此生不再回去,冷漠着它的今天和明天;二是当我们的城市人生遭遇困顿或者有闲情逸致的空闲时,我们开始回忆乡村生活的淳朴和美好,我们用彩色滤镜和乌托邦想象去回忆那一切,为自己疗伤和怀想。
我不知道别人是否如此,但我是,面对如母亲一般日渐衰老的乡村,要么冷漠待它,要么拿它疗伤。中年以后,我才懂得我的自私和我对生我养我的乡村的无礼和亏欠,我才懂得乡村不仅只有过去以及对过去的回忆,每一个乡村都有它独一无二的现在和未来。
直到中年后,我走过一些乡村——自己的和别人的乡村后,我才有所明悟:无论我多么小或者多么老,我都是乡村的孩子。我的精神离不开乡村,源自我对乡村记忆存在那种无法割舍的依恋。这种依恋,心理学上叫“怀旧”,地理学上叫“恋地情结”,医学上叫“思乡病”。只有不断回到乡村,这种依恋才会落地化解。贾平凹先生将故土称为“血地”,很有道理,那么,我的江汉平原的乡村是我的“血地”,我所寓居的福州是我的“汗地”,我所渴求去往的一切乡村是我的“魂地”。
天下乡村无一不是我魂魄的安妥之地,因为每一条乡村的路都可以通达我的故土乡村。李清照说:故乡何处是,忘了除非醉。
(作者系天门九真人,现居福州。)
扫描二维码
在您的设备上浏览本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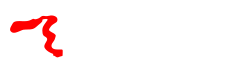

 鄂公网安备 42900602000102号
鄂公网安备 4290060200010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