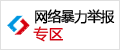酥饼漫忆
◇朱青苓
一闲下来,我就像小孩子,老捞零食混嘴。如今这零食真是五花八门,敞开肚子可以吃它个天南地北。
前不久,好友曾和我说起:在广东的侄子独独要快递家里的饼子给他。现在偌多好吃的,你说怪不怪。饼子,不就是酥饼?我的记忆被激活。细细盘点,这枚酥饼,连同岁月的印痕一直搁在我心里。我想说一些有关酥饼的往事,回味它蕴藏在心间的些许酸涩丝丝甜香。
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。是的,我的家乡——江汉平原一隅,土地平展肥沃,十分利于种植冬小麦。一度,这冬小麦曾是家家户户做粑粑、打酥饼最初的原材料,且打酥饼的习俗一直持续多年。
春天,一望无垠的绿油油的田野里,小麦随了雨水滋滋拔节,迎着太阳汩汩灌浆。阳光懂得农家的心思,狠命地催促麦穗快快饱满金黄。
“立夏三天连枷响,小满三天粑粑香”。“小满”节气里一夜南风,“小麦覆垄黄”了,农人铆足劲儿与太阳比赛看谁起得早,淌着热汗跟老天抢时间,满怀希望向季节要收成。
夏天做粑粑可以算是打酥饼的前奏。做粑粑这原始简单的方式,是乡亲们没日没夜一个忙季后对自个儿最粗糙的犒赏,也是对土地母亲慷慨馈赠的朴素感恩。况且,人是铁饭是钢,吃两碗“焌米茶”(本地夏季主食),扭身就饿哒,各家就把自留的小麦磨出细面粉,做粑粑(别的地方有严格的分类说法:馒头、包子,这一带统称“粑粑”)。
夏天气温高,清早和好面,下地干一上午活,中午回家吃饭休息的空档,和好的面做成各自喜欢的样儿,放蒸笼里饧一下,后大火猛蒸。不一会儿闻到香味,洗净手,揭开笼盖,手上蘸点冷水,在粑粑身上按按,拍拍,粑粑迅速弹起。端出来,那些大小型号不等的蒸笼里,长条如窄枕、圆嘟嘟似乳包的粑粑趴满圆圆的一格,松软软,香透透的。
冬天打酥饼。辛劳一整年的农人,得以有空闲真正坐下来,将生活变一变花样。
先前晒干后入大缸、进小仓(自制的装粮食的木器)的小麦,这时候舀出一斗两斗,用大竹篮装了挑到河里淘净,尔后,晒席摊晾。一些有经验的老人总会提醒年轻的媳妇们:拣几粒放嘴里咬一咬,粘牙的湿了些,还守着晒会儿。咯嘣响的是晒得干了,加工的时候别忘了喷一点水。不粘牙或不咯嘣响最合适,这时候收拢,磨出的面粉多又白,打出的酥饼口感细腻。
打酥饼一般选择不上工的时日。不仅家里人参加,还“兴师动众”,无疑是年节里最隆重、最有仪式感的一次集体手工大操练。
主人家早早就请好做酥饼的师傅。充任师傅的,多是有实践经验的伯伯婶婶。
小孩子时不时地追问,大人默数天数,这一天来了。
主人家搬出早就磨好的面粉,称好斤两,按比例配上食用油(产棉区吃的都是棉籽榨的油)和红糖(甘蔗制成的红砂糖好看又香甜),师傅用起来得心应手;若是师傅喊:拿油来!主家慌里慌张,性子直的师傅会嗔怒:咋回事,怕我带走?
炒酥是第一步,也是关键一步,火候合适,酥就炒得好,炒嫩或炒老都会影响口感。师傅一定会小心地拿捏。这样,炕出的饼香甜酥脆,咬一口,焦黄的外皮碎屑直往下掉,入口就化,甚是好吃。但做这样的饼,主家需舍得,原材料不得折扣。多数人家都会备充足,把所有原料都摆出来,听由师傅摆布。少数家底薄、劳力少的,免不了会在棉油、红糖这些要用钱买的物资上折扣一点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师傅也无奈:就这样吧,做什么吃什么。大家心知肚明,显然埋汰了师傅手艺。
铁锅洗净,灶膛烧燃。师傅把称好的面粉和棉油倒入锅内,边叮嘱灶膛添火者,边双手不停地焙炒,看好火候,适时起锅。
酥炒好了,接下来和面。热水和面粉调和,需用力揉,反复揉,出力气身上发热,师傅就脱了棉袄,撸起袖子把面团揉得软和和。随即,在案板上来回揉搓成长条均匀的圆柱状,一只手握着,另一只手揪成大小一致的小面坨。
等候在一旁的主人全家、姑姑、大姨、小舅正式开始流水作业了,包酥的,擀匀的,包糖馅的,各就各位。小面坨里包酥,小孩子学着做,内行些的用师傅带来的擀酥短棒专心擀匀,再包红糖馅(糖馅得掺少量面粉,以防糖快速融化流出),灵巧的手拈一撮糖馅,放在擀好酥的面坨正中,再小心地捏拢不留缝隙,最后用手按压扁平。若马虎了事,炕时,酥饼里的糖化了流出来,糊了饼身不好看不说,少了甜味不好吃。每每包糖馅时,师傅就守在旁边,边示范边提醒:手慢一点不打紧,要包合缝,包好看。
不一会儿,一溜人的杰作呈现,一枚枚圆圆的浅黄的饼,一圈圈整整齐齐码放在大号簸箕里、案板上。大家不约而同望着,会心点头:蛮好蛮好。
冬日的白天短,一屋人这么一忙活,往往就到了下午两三点。小娃子家早等不及了,屋外头疯玩一阵又溜进厨屋,打探情况。若是见饼被码进平底锅,断不会再出门,守在厨屋,一眼不眨地看师傅抓住锅盖顶端把手上系的粗而牢的绳子,提起那两面中匀铺着草木灰,被三个厚铁钳牢牢钳住三处边沿的厚锅盖,稳稳地放在灶膛放锅的圆口上。师傅一声令下:可以点火烧盖子啦!主人自不敢怠慢,赶紧烧燃豆梗之类的专门柴火。约十来分钟,师傅低头往灶膛内一瞅,锅盖内透红,便吊起锅盖,另一人端来装了饼的锅放灶面,迅速把吊起来的锅盖盖在锅上。
靠着锅盖的热力,不一会,一阵酥糖混合的香味弥散在不算宽敞的厨屋里,迅速蹿向屋外,香甜味诱惑着所有人,你一个,他一个,小孩子几个,打屋外头路过嗅到香气的本家,身子晃晃:炕饼子啦?屋里头赶紧招呼:来哟,尝两个热饼子!
热酥饼,香喷喷,酥脆脆,甜津津。小孩子管不住嘴,一口气吃了三五个,大人就拦住:吃不得啦,热饼再吃就坏肚子了!有不听的,大人顺手夺了:讨打吧,吃多了真要害人的!有酥饼吃,就是过年,伢子们哪禁得住嘴?
你尝他吃,炕出的第一锅所剩无几,或一个都不剩。主人也乐意。若是家底薄的,亲友们也体谅,象征性地尝一个。
包的包,炕的炕,几锅后,酥饼的热气也散完了,随即,主人家便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:包封。这包封,由包得扎实好看的人担任。包封用的纸,事先就买好了,浅紫红色,厚些的2角一张,薄的1角2,若是有亲友在学校或其他单位,就早早向亲戚讨要报纸。备好的纸裁成大小一致的带长方形的样儿,拿出一张平放,再数上10个饼并列靠拢在纸的一边,一只手管住,另一只手帮忙顺着纸张裹成圆筒状,最后用糨糊在筒身封口。两筒称之一合。纸充足就多封,至少得保证能在拜年走亲访友足够。剩余的没纸包就设法用干净的坛子或罐子装好,留作过年待客的茶点,也算充当零食。
眼下,酥饼仍是乡亲们饿了随取的零食,始终应急方便。早早出门赶工,酥饼就当快捷的早餐:鸡蛋煮酥饼,可口又营养。而那烧红了底部的锅盖,那大号的圆圆的平底锅早没了踪影,隐没在记忆深处了。
因为疫情,就地过年。“这里什么都买得到,就是没家里的饼子。还是嘴贱啊!”家里人听得明白,快速上街买,包装好给那边寄过去,快递费都快赶上买酥饼了。那边的身处异地他乡,在这团圆喜庆的节日,接了酥饼咬一口,味蕾和甜酥接触时,舌根与家乡连通了,打工的辛酸,分离的苦楚,经由这酥饼于齿间咀嚼,酶化成圆圆酥酥香香甜甜。
平原上的麦浪是否会在他们眼前起伏,父辈弓身握镰的背影是否还在他们心头跃动?不得而知。反正,他们想吃。
我把酥饼搁心里,一回味,便有香甜泛起。
扫描二维码
在您的设备上浏览本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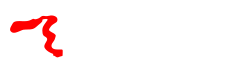

 鄂公网安备 42900602000102号
鄂公网安备 4290060200010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