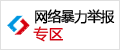相伴
◇龚春霞
随着我们一个接一个离开佛子山,外出求学、工作,来到小城生活,父亲退休之后也和母亲搬到了城里。转眼间,他们已经在小城生活了近二十年。
在他们居住的院子里,谦和的父母和周围的邻居相处非常好,有个什么事情,大家都互相照应。最初那几年,天气好的时候,吃过中饭,父母会结伴到附近的小茶馆打打麻将,偶尔输个三块五块心疼得不得了,歇几天手再去。母亲在屋前空地上开出几块菜地和花圃,种些时令小菜,栽上各种花草。种出的菜,隔三岔五步行送给我们。逛街时,母亲会扯一点自己看中的花布,拿到服装店量体裁衣,做出新衣。
年轻的时候,他们被困缚在家里,与贫穷作斗争。进城后,在孩子们的策划和陪同下,先后去了北京、武汉、杭州等地游玩。
艰难拉扯六个孩子,在望眼欲穿中各自有了饭碗;又在殷殷期盼中当上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;而今,还添了重外孙。他们,有过好时光吗?也许,现在才是他们最好的时光:不担心生产队超支、不担心灶上揭不开锅盖、不担心上学凑不齐学费、不担心送不起人情;超市随意进,广场随意逛,丝丝缕缕的好日子来日方长!
从年轻时起,哮喘就伴随了父亲漫长而艰辛的一生。近十多年来,每到冬天,卧床不起,吃穿都靠母亲服侍,稍有动弹,喘得上气难接下气,脸也憋得青紫,非常难受。偶有个难得的好天气,母亲就推着他到户外晒太阳。二姐和三姐前几年外出,临行前都蹲在父亲床边,泪眼婆娑,怕回来时,再也没了亲爹。
母亲总说父亲这一生过得苦。年轻的时候,要拉扯众多的儿女。总算儿大女大,不用操心了,可享享清福了,却被这个病缠住了。
而她自己,也被父亲的病缠住了。小区的婆婆们打打牌,她不能;跳跳舞,她不能;她要陪伴她的老头子。她去菜场买菜也是火急火燎,即使是片刻,她也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家。他猫一样小的饭量,却常常突发奇想,要吃点这,吃点那,母亲一点儿也不嫌烦,东边的菜场,西边的超市,尽力去满足他。费尽心力做好了,端到他面前,他已经没胃口了。母亲气得骂他刁,嗔怒他会害人,父亲从来不吭声,含笑望着母亲,脸上是淡淡的宽厚的神情。
父亲很幽默,话不多,但语出惊人。有天过去看望二老,父亲躺在床上,我说您想吃什么我去买。父亲抬起头,笑眯眯说了两个字。我没听清,又问了一句,父亲依旧笑眯眯地:“吃睡!”真是个可爱的老头子。
曾有一次,父亲突然敞开了心扉。他说:“这病,真的太难受了。我好想死了算了。但想一想,又不能死,得给你母亲做做伴。再说,好歹还有几个退休钱,你母亲用起来也宽裕些。”
父亲不能走,她扶他上厕所;父亲没牙齿,她做两样的饭菜。但多半时候,端给父亲时,嘴刁的父亲只闻一下,便示意端走。她不得不出去到街上再找面条、米粉、馄饨等食物;父亲不能自理,起床睡觉都需要母亲穿脱衣服,捱被子、添减衣服,母亲像对待婴儿一般,一旦呼吸急促,赶紧插上床边的吸氧机,不曾丝毫怠慢;父亲做过前列腺手术,尿袋不离身。导尿管更换、冲洗,母亲也学会了。门前的铁丝上,常年洗晒着大块的布尿垫。
母亲如此全能,又任劳任怨,常说她就是父亲的高级保姆,只是没有拿过一分钱。父亲有时候气喘得匀,会幽默回击:“您是家里的财政部长,一分一厘全归您掌控。”天气晴好时,母亲会再三地动员父亲起床,再各戴一顶遮阳小帽,于是便可看见一个矮胖的老妇人,携着茶杯,推着轮椅上衰弱的老头子,在附近转悠转悠。
门球场最近,过街即是。那儿有绿树,有健身器材,有弯弯曲曲的水榭。母亲坐在水泥矮墙上,与老人们家长里短;父亲总是安静地坐在轮椅上,用右耳仅剩的一点听力,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。
也常常穿过一个十字路口到西湖去。母亲爱花,屋前栽植了几十盆各种各样的花。一路上,她很有兴致地观看着花草树木,不时地停下来指点给父亲看,一字一句地念出木牌上的油漆字,似乎轮椅上的老中医是个不识字的文盲。
正月里的一个周末,暖风暖阳,我们煽动父亲起床去转转,透透气。父亲睡在床上,望着我们,含着声,不置可否。母亲有点生气:“平时我要你起来,你像以为我是要害你;今天你的伢们叫你起床,她们还害你不成!”
父亲没有了牙的嘴一瘪,笑了一下:“多穿点!”
母亲见状,脸上绽出欢喜的笑容,不过还是抢白一句:“生怕冻死了!天冷哪个会叫你起床!”
我推了父亲,大步往马路上走,父亲开腔道:“等等!”
我问等什么,父亲说:“等下她。”又补充道:“等你姆妈一起走。”
母亲提着袋子、水杯、小马扎从楼门里出来,备齐粮草兵马,好像是去长征。
老公推着父亲,母亲轻松多了,她照例把路旁的花和树一一指点给我们看,明明是无数次路过见过的,却仍然兴致盎然,让我觉得她像一个回到春天里的少女,心底里单纯地装着美好的事物。
我们在茶经楼下停下了脚步,准备在这儿休息休息。父亲突然向母亲伸出手去:“拿来!”
我以为父亲要喝水,赶紧拿过母亲一直提着的无纺布袋,要找水,结果父亲一把扯过袋子,双手用力地按在腿上,再不吭声。
母亲见我不解,笑眯眯说:“他怕我累。”
那一瞬间,我为自己的粗心羞愧了;同时,为发现了父亲母亲间相濡以沫的温情而开心。
母亲这般日复一日地照顾父亲,不曾歇息过一天。如此身累,心也累,她却逐渐地成了一个体态雍容的老妇人,并且时常因为过于肥胖而伤心。附近的老婆婆没事就三五成群地扎堆,东家长西家短,也跟年轻女人一样,老是为谁谁的新衣服新发型发起议论。母亲自尊心极强,尽管有儿女们不时孝敬四时新衣,却在穿衣服不好看这件事情上极度自卑。
父亲常常坐在一楼的阳台上,默默地看小区里人来人往。他这样安慰母亲:“您是这院子里最好看的婆婆!”
这一句话,肯定鼓舞了母亲至少半年时光。
有一次吃饭,见母亲左手虎口处写着一个“我”字,蓝色圆珠笔写的,硬币大小。我问她怎么回事,母亲还没开腔,父亲抢先说道:“她是要预防老年痴呆症。万一迷路了,别人问她叫什么名字,她就把手一伸,说,叫‘我’!”
母亲被逗得笑了起来,笑得忍不住,拿筷子的右手直揉眼睛,讲给我听:“昨天看电视,电视上放着听写汉字的比赛。你大大说考考我,看我还会不会写字。一时找不到纸,我就在手背上划了几笔。你一问,他就故意那样埋汰我。”
坐在饭桌边,我不禁欣赏起这两个老人:一个曾经家世不错的男孩,幼年失怙,少年多舛,年轻时绝对玉树临风,游走江湖,悬壶济世,清高的骨子里游走着谨慎,也游走着聪明与幽默;一个命大,十一个同胞,只活了她一人。年轻时也应该不丑,因为现在一头微卷的银发,让她那么像银屏老明星田华老太太。
父母平时的奢望就是孩子们过去陪着说说话。每到双休,兄弟姊妹聚到父母家,搞卫生的搞卫生,烧火的烧火,十多人围着大圆桌吃饭,聊天,有时候还有一桌小小的麻将。屋子里人进人出,欢声笑语,这种热闹,父母又喜欢,又盼望。每次还未到周末,父亲就开始过问,谁有没有事,谁能不能来。日子就在有望的等待中过去了。
大家心疼母亲年迈体弱身累,屡次提议出资让他俩入住养老院或请保姆,母亲死活不松口:“你们的大大别人伺候不好的,麻烦又多,脾气又古怪,换个外人来,哪个能像我这样耐烦,只怕没过两天,就板阴砖了!”又说:“养老院不会去的。我还动得了,我来安置他;我动不了了,到时候再听天由命。——他死在前头是他的福气,要是我死在前头,该他造活业。”
因脑出血几进几出医院,父亲走在了前头,八十岁,他终究做了那个有福气的人。临终之际,儿女环绕,他已经说不出话,却目不转睛、久久地望着母亲。直到有人领会到他的意思,说:“您放心吧,我们会照顾好姆妈的!”他才慢慢合上了眼帘。
父亲人世间最后的凝望,是属于母亲的。他把此生最后的告别给了母亲,把此生最后的深情与牵挂,给了他的最好看的婆婆!
自父亲去世后,母亲不再那么劳碌,身体却渐渐消瘦了一些。她说,以前父亲吃剩的不吃的,她都吃了,不胖才怪;现在,不用吃那么多,自然瘦下来了。
她常常翻弄那些花花绿绿的相册,哪张照片上父亲是四十多岁时照的,那时候生活艰难,父亲瘦得没有人形;哪张照片是在故宫照的,父亲和她穿着皇帝皇后的服装留影;她一遍遍地讲述父亲的轮椅曾经卡在哪儿,路过的年轻人帮他们将轮椅抬上台阶,嘱咐我们遇到老年人,要伸手帮忙……
农历七月半,我们几姊妹一起带母亲回老家,去父亲的墓前祭奠。母亲一路沉默,到佛子山老街时,她突然喊停车,径自去路边小餐馆买了一碗粉,我们都不解,问她是不是饿了,她低声回应:“你们大大”突然哽咽起来,“喜欢吃粉,走的时候,什么都吃不进去了……”
国庆节后,一夜之间由夏入冬。这几天,气温缓缓回升至20度左右,秋天回眸而笑。桂花树突然惊醒了一般,赶紧将香囊尽数抖擞,在满城浓郁的桂花香阵里,母亲的屋前继续开花。这些花,有邻居给的,有我们买的,也有许多,是她推着父亲散步时摘回的花籽种下的。那些相伴的晨昏,她推着他,走走停停,看见花儿便会凑过去,指着花丛间立着的木牌,认真地将花的名字念给他听,仿佛他是一个不识字的老中医。
扫描二维码
在您的设备上浏览本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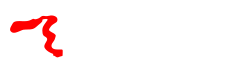

 鄂公网安备 42900602000102号
鄂公网安备 42900602000102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