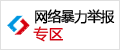割草
◇汪文玮
我对青草,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。
每当徜徉于田间地头,漫步在公园、广场,看到碧绿、茂盛、蓬勃生长的青草,情绪就会莫名地激动,年少时与同伴割草的情景就会在脑海里鲜明地浮现。假如那时候我们遇到这样蔓延的青草,该会怎样的欣喜若狂啊!
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,农业机械是稀罕物,人们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集体劳动,每个队喂有牛马等牲口,耕田、犁地、拉车,牲口是得力的帮手。牛马吃草,割草的往往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,大人要到田里干农活。
那时候学校似乎没有作业、考试,更没有考试排名、补习班、兴趣班之类的。我们有充足的课外时间、长长的假日。
夏季是野草疯长的季节。放学了,放下书包,呼朋引伴,三五成群,割草去。翠兰、春枝、青娥、喜贵,我们不约而同,组成了割草“小分队”。
青娥年纪稍长,她一声吆喝,我们挎上竹篮,拿着镰刀,跟着她在村子四周东溜西转,寻找目标。池塘边,沟渠旁,小路上,我们头顶烈日,你追我赶。
有时站在水中割,水淹没了膝盖,腿上钻进蚂蟥,一数,七八条,几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,互相加油、壮胆,揪蚂蟥,血直流,虽害怕,但不会哭。半天工夫,篮子满了,我们唱着歌儿,兴高采烈地回家,像凯旋的战士。
大路旁割草,不必担心有谁驱赶,可是那里的草一遍遍割,几乎绝迹,怎么办呢?只好向棉花田里进军了。
夏日的棉田,棉苗比腰高,放眼望去,一片绿海。生产队的田有专人管护,以免割草的人损坏庄稼。记得一个凉风习习的午后,青娥领着小分队,潜入棉田,田里的草不算旺盛,我们蹲下身,用手扯,用镰刀割,用铲子铲,一把把的青草装进了篮子。突然,“管护佬”从天而降,我们落荒而逃。
翠兰挎着篮子,在前面飞奔,喜贵丢了竹篮,挥舞镰刀,紧随其后。我本来跑不快,又不忍扔下“拖油瓶”,“管护佬”紧紧向我们追来,离我越来越近,我害怕之极,吓得半死,便随机匍匐在棉田,一动不动,只听到心突突直跳,“管护佬”像一阵风从我身边呼啸而过,我逃过一劫。
秋冬时节,草木枯萎,没有青草可割,我们放学后主要是拾柴火、捉迷藏、玩扑克。
大地回春,春暖花开,田野的草复苏。春枝带队,我们到邻村割草,邻村割草的小伙伴维护自己的领地,和我们打嘴仗,我总是站在前面,理直气壮,口若悬河,还得了一个“铁嘴壳”的外号。
附近没草可割,我们到十里开外的白茅湖农场去。挑选个风和日丽的日子,挑上担子,带上干粮,迈着轻快的步子,向地广人稀的农场奔去。“草盛豆苗稀”,草似乎挥动手掌招呼着我们,我们弯腰伏地,汗流浃背,热乎乎的青草躺在了我们的担子里。
累了,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坐在田边,小憩片刻,喜贵领着我们数手上的螺,“一螺穷,二螺富,三螺四螺住瓦屋”。每到这时,我的心就会涌起无限的遐思与畅想,我是二螺,似乎“富贵”又遥不可及。
牛归圈,鸟归巢,我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,满载而归。回家一瞧,手脚都起泡了。
草过秤给生产队,可以换工分。把草晒枯,藏起来,冬天还可以偷偷拿出来卖钱,公开卖是资本主义尾巴,要割掉的。在物资奇缺,靠工分吃饭的岁月,割草意义非凡。
而今,曾经一起割草的小伙伴已成为奶奶,割草已成为我生命中珍贵的记忆,成为沉淀在心中的一种情怀。每当行走在高楼林立的都市,看到都市一角的青草,我就会穿越时空隧道,想起儿时割草的一幕幕,就有了战胜困难的力量,就会告诫自己:热爱劳动,热爱生活。
(作者系天门人,天门中学教师)
扫描二维码
在您的设备上浏览本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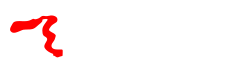

 鄂公网安备 42900602000102号
鄂公网安备 42900602000102号